潘客印對曾敬驊的第一印象竟是「沒有覺得他帥啦!」2人第一次聊天,他只覺得曾敬驊「眉毛很粗」,但聊完後卻發現,他笑起來雖然很陽光,內心卻很沉穩,甚至有時候讓導演覺得:「到底是我大他10歲,還是他大我10歲?我要稱他一聲哥哥的感覺」。導演看見曾敬驊「有對外的一面也有對內的一面」,認為他與角色的內心拉扯十分契合。

當得知電影取材自導演的真實故事後,曾敬驊直言:「我覺得他蠻勇敢。」他坦承,起初因為擔心觸碰到導演的痛處,不知道該如何靠近,感到非常掙扎。直到導演告訴他:「他沒有要我成為那時候的他,他希望是透過我的特質去跟這個角色融合在一起。」這句話才讓他放下壓力,專心投入表演。
而導演潘客印也坦言,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,其實也是在療癒自己與家人的關係。他過去為了讓姊姊知道家人的愛,主動為家人創造美好回憶,「因為我知道有一天家人也有可能會不在,所以我希望把這些回憶留著,我之後就完全沒有後悔,即便遇到什麼天災人禍把我們分開了,但是至少我們的那個美好,我曾經主動去創造了,而且都在我們心裡,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,成為我們美好的回憶。」

黃珮琪成長於單親家庭,對於爸爸偏向軍事化的教育方式,感到非常不理解,「為什麼感覺別人家裡面的狀況都好像很和樂融融?」有一天,她在打掃時,打開爸爸的櫃子,意外發現了一本書叫《如何跟孩子溝通》,讓她意識到爸爸其實有那份心意想要好好溝通,「心裡面會酸酸的」。後來有一次生日時,爸爸傳簡訊給她,上面寫著:「妹妹生日快樂,爸爸愛你。」從小到大從未聽過爸爸說「愛你」的她,當下看到這句話時,「整個大爆哭」。

曾敬驊則分享,他在青少年時期有一段非常叛逆的過程。當時的他會翹課、晚回家,甚至讓學校的警告累積到三大過。他坦言,那時候會覺得:「為什麼別人家不會這樣,我家要這樣子?」他覺得父母的管教是一種限制,也感到不解。然而,隨著成長,他逐漸理解了父母的愛。他體悟到:「他們不知道怎麼表達,因為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式靠近你。」
現在的他,會選擇用更直接的方式表達關心,他會直接為父母安排休假,帶他們出遊,或是約上來吃飯。他也會幫父母協調工作,讓他們減少批發的業務量,但仍保留早餐店,「有時候你突然把它抽掉,他們會不知道幹嘛」,像他阿嬤以前在市場殺魚,現在還是會每天走過跟人家聊天,因為「那是他們的生活圈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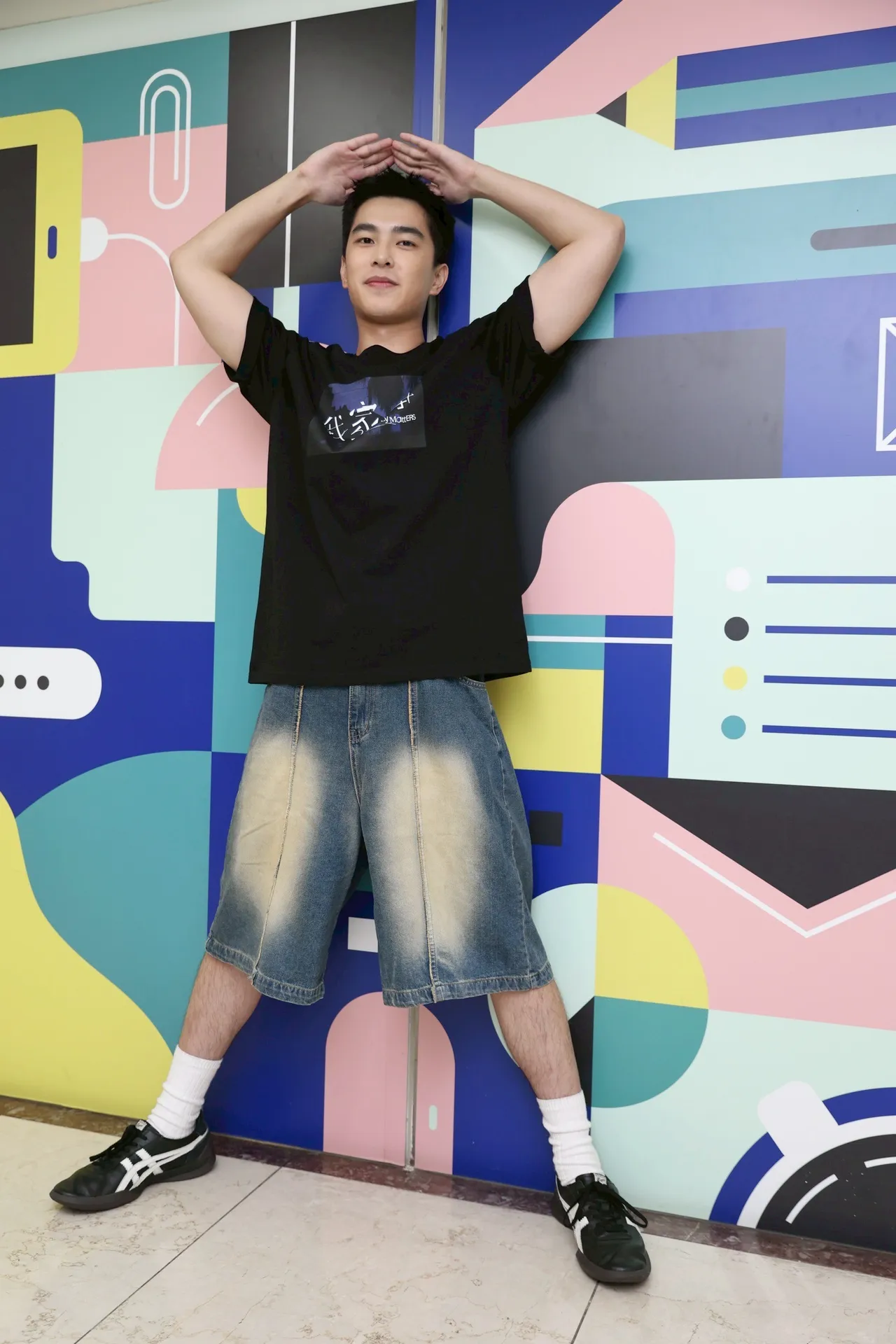
兩位演員的私下生活都很充實,黃珮琪自稱是「狗媽媽」,養了兩隻狗,把屎把尿樣樣來。雖然收拾滿地棉花、被咬碎的娃娃是日常,但她仍覺得養狗非常療癒,「去狗狗公園,有時候就會放空,看狗狗在玩,就覺得當狗真好,下輩子也要當狗」。而曾敬驊則是熱愛下廚,「我很愛煮菜,我會去看食譜自己嘗試在家裡做菜」,而他的拿手菜是爌肉(滷肉),他笑說:「這個我有信心。」

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