該名女子在臉書沉痛控訴,她去年9月在車上遭一名導演性騷擾,事後曾向時任婦女部主任許嘉恬求救,但對方態度消極,甚至反問她「當下妳為什麼不跳車?」、「妳怎麼沒有叫出來?」、「所以呢?妳希望我做什麼?」
受害女子解釋,當時她坐在座位中間,根本無法跳車。陪同的同事也緩頰,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那種情況下自我保護。不料許嘉恬回應,「那妳們可以利用午休時間一個小時啊,去對面華山大草坪也好,手牽手一起練習大叫,甚至練習從我們部門大叫喊到前面民主學院。」
受害女子指出,許嘉恬之後告訴她「只要程序一啟動,大家都會知道妳被性騷擾,妳也知道黨部就這麼小,妳的名譽可能會造成受損,妳要考量到這些後果,以及妳有沒有辦法承受,妳確定要我去跟媒創中心講這件事情嗎?」
主管的這番態度讓她心寒了,她痛心表示:「我是帶著熱忱進來民進黨,帶著傷和遺憾離開的,我失去了眼裡的那道光,直到現在仍在療癒。」
全文如下
為時已晚但也該被好好接住的求救信
「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,好不好?很多事情不能就這樣算了,如果這樣的話,人就會慢慢地死掉,會死掉。」
好遺憾曾經的主管,婦女部主任許嘉恬在最該是我後盾之時,選擇轉身離開。時隔多月了,以為能放過自己的,近期看人選之人時又無數次的翻江倒海襲來,我又哭到差一點死掉。
而我現在才有勇氣整理好思緒,好好說出來。那是一個我主責的專案,攝影團隊回程的路上,導演趁著大家上廂型車,昏暗欲睡長途之際,對我實施了性騷擾。他將我的頭摁上他的肩,讓我靠著睡,我嚇傻了,不知道該如何判斷當下的狀況,他覺得我疲倦,出於關心嗎?他知道我是學生,是長輩的關心嗎?我竟下意識的,恐懼到將此合理化來安慰自己鎮定下來:不是的,應該是我的錯覺。
爾後,在一個顛簸中我藉故起身,尷尬地看著他(期間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睡著),他寒暄道,累了吧,看你很疲倦,手又撫摸上我後頸,在下巴肩頭與胸上游移、愛撫與按摩。我後來低頭看手機試圖盡我可能保持距離,而我仍感受到他熾熱的視線,我不敢回頭,直到他的工作室。其他團隊人員在外頭陸續卸器材,他抽著煙,目光不曾放過我,他邀請我進去坐坐。我忍住快哭出來的樣子,但我想那時我應該很僵硬,就這麼站在大廳裡面,他來回巡著內外狀況,又回來我身邊,問我有廁所,要不要去廁所。
逃無可逃之際,我躲起來了。我一進廁所立刻反鎖門,跪在邊上止不住乾嘔,我還怕他發現有什麼不對勁,拚命忍住不可發出異音,因為我聽到了,他在門外的踱步,以及像提醒著他存在感的清喉聲。腦子一片空白,但直覺知道我可能的下場,等不到我後怕,我在聽到門外腳步聲多了,才敢走出去,此時我工作還沒結束。
直到上捷運回家的路上,所有緊繃神經慢慢鬆懈,我才顫抖的打給同事求救,我慌張到語無倫次,她好好安撫下我才能拼湊起來,現在在回憶這些,對我而言也是難受的。而之後在我們決定上報主管,當時的婦女部主任許嘉恬時,我的主任不僅第一時間總在不是重點的地方,放大我被性騷擾的細節要我做回憶陳述,也在聽完後,冷冷的反問我,所以呢?妳希望我做什麼?
我以為我抓到了浮木,卻又是更高的駭浪。我羞愧我內疚,我為何一個專案負責不了的情緒四溢,這是在她第一時間該同理我、給我專業意見之時,給我罩下的的遮羞布。我好像不該感受難過、不該生氣、不該大驚小怪,因為它就是工作,所有被否定的情緒嘎然而止。儘管最後她補上說黨內也能走程序,但也就草草收尾,也未立即讓我停止負責此專案,只重複著強迫我要做什麼決定(儘管此時仍未跟我清楚解釋完程序),她說了解後再找我談,但我當下已失去了信任感,失望的離開了會議室。
第二次再與主管面談,由於我情緒還在高度恐慌,同事陪我前往她所在的咖啡廳,我不知道我還會面臨什麼。她試圖營造輕鬆的氛圍,對我說,有時候我忘了妳還太年輕,看到妳的工作幹勁總會想到我年輕的時候,然後也提到她過往選舉時被性騷擾的經驗,再接著問及我的這次經驗,說了對我最為錯愕的:那你當下為什麼……不跳車?我不懂,你怎麼沒有叫出來?
我好想離開。同事立即委婉地告訴主任,並非所有人都能在那種情況下,有意識或者有能力去做自我保護的(在這之前跟主管說明的過程裡,我也都明確說過我位於座位中間,根本無法跳車,就上高速是能跳去哪裡)。而我們主任給我們的回饋卻是,那妳們可以利用午休時間一個小時啊,去對面華山大草坪也好,手牽手一起練習大叫,甚至練習從我們部門大叫喊到前面民主學院。之後的閒話家常我已經超載了,任何事情好像都可以很輕鬆的四兩撥千斤來定論,飄飄然的肉身,支離破碎的靈魂。
她又陸續找我與談幾次,她要我儘快做決定,她才能幫我。那時還在混沌與迷茫間掙扎,且聽她說道,當然黨內有程序,我們也可以走程序,但我相對就無法幫妳,妳也要理解我態度可能比現在在更冷漠,因為我要公正客觀。
我在這態度前躊躇,但我真心不希望再出現和我一樣的受害者,所以想著至少要告知媒創主任。而她後來幽幽告訴我,只是無論程序一啟動,或是告知媒創主任一人也好,大家也會知道我被性騷擾,你也知道黨部就這麼小,你的名譽可能會造成受損,你要考量到這些後果,以及你有沒有辦法承受。
你確定要我去跟媒創中心講這件事情嗎?婦女部算來算去也就那幾個同仁,大家想一想算一算也知道是誰。
那我知道意思了。話講到這份上,我輕聲闔上辦公室的門。
至始至終,有關這件事我一通主管的關切電話皆未收到,而同事卻收到了一堆電話關切,被主任問我有沒有跟同事散佈她的謠言。就連我可能需要的社工聯繫資訊,她都是傳給同事,讓同事轉傳給我的。選舉結束離開後,某次我才得知,連我那時的身心就診都可以由黨部支付,而這些資訊我當時完全沒有得到。我難過地告訴同事,我是帶著熱忱進來民進黨,帶著傷和遺憾離開的,我失去了眼裡的那道光,直到現在仍在療癒。
無力感越來越重,在某種大局當前的氛圍與壓力下,我現在才能理解與接受,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,我壓根沒有錯,而這絕對不是自私。前主管曾詢問過我是否有被性騷擾的證據,我說我沒有;可我想,我現在所陳述的這一切事實與感受,就是最好的證據。我要撐不下去了。在潰爛之前,再痛我也想腕掉。
這次,我選擇為自己勇敢。我想再次相信這個世界,相信公平,相信正義,相信人與人能被理解,而不是「我忘了妳還太年輕」:並非我太年輕所以我要承受這些「成長」,這不是為我好。
這樣的人如今是黨中央的副秘書長。當時高舉著婦女權益旗幟的人未成為我的翁文方,我就要成為我自己的翁文方。
謝謝大家看到這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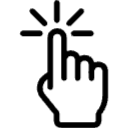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