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舒湄今在臉書PO文說,她貼出第一篇文後收到很多Me Too來信私訊,有許多人告訴她,因為「同一位加害者」的霸凌,她們也出現身心症狀,必須接受諮商與治療,是促使她決定說出來的主因,一開始不想說,是因為害怕被業界封殺,「我也確實在這之後,曾被從工作候選名單中給撤換掉」。
她並透露,原本今晚要出席北影的開幕活動,「我想看九把刀的電影,6/12已回填出席表單,當時的我並不知道我6/15會發文,但至目前為止仍未收到北影回覆入場的電子票券。 所以我不知道該不該去」。 聽聞周遭有聲音傳出「誰敢再找你拍戲」、「掃到電影圈盛事等於跟全電影人作對,你完蛋了」,她堅定說:「沒關係了。 我未來的人生與工作,不管好與壞,反正,牙一咬,就過了。 『我不想成為像他那樣的大人』」。
黃舒湄稍早宣布今晚6點30分在中山堂門口接受提問。北影總監李亞梅表示不知情,至於黃的文中提到有權勢壓迫,迫使台北邁斯納工作室改動聲明,李亞梅說:「我們也沒有打電話給鳳小岳的邁斯納,她認為邁斯納改聲明是受到我們的逼迫。剛剛鳳小岳有打來說,是他們覺得自己聲明不夠清楚,所以重寫。」

黃舒湄臉書全文:
《我說,我勇敢說》
首先,
我想告訴所有的 被害者 以及 我自己:
「不需為加害者的惡行負責」
「不必因說出來而感到抱歉」
「嚴格」VS.「霸凌」,兩者完全不同,請辨明。
《為什麼現在才說? 》
「害怕被業界封殺」,是我恐懼的壓力之一,我也確實在這之後,曾被從工作候選名單中給撤換掉。
做出決定之後,才驚覺電影盛事開幕在即,原本打算7月閉幕後再行說明,但,說與不說,都各自影響不同的層面無法拖延,天人交戰,掙扎至今,望請各界理解。
(以上白話翻譯:說不說、什麼時候說,我都會被罵,,,想罵之前請您看文章 第一段吧。 )
《關於執行單位》
加害者必須為他的惡行負責,
執行單位也必須為師資的選擇負責。
第一堂課,這位老師就對同學們說:
「我本來不想教的,教編劇可以,但是教『表演』? 但同仁們說我可以教,就硬推我出來教。」
執行單位從專業角度挑選師資的評估是什麼? 是權勢? 是真專業? 還是其他考量?
並且應為其所選擇的師資及課程發生的事負責。
《關於「台北邁斯納」》
台北邁斯納工作室所發表的第一版聲明,讓我感到同理支持並且被接住,但是之後再修改過的澄清版本,就彷彿把那拉著我的救命繩索給切斷了。
會修改聲明,是否也受到權勢壓迫的影響呢?
本事件工作坊的「初階班」,是由台北邁斯納工作室的Martijn老師所教授,至「進階班」才轉由霸凌事件的當事老師接手,而這位當事老師在授課過程中,不斷提及台北邁斯納、Martijn、以及 鳳小岳先生⋯⋯作為授課範例。
基於該當事執行單位具有官方色彩及業內代表性,且本工作坊的同學,許多是上過初階班、甚或是台北邁斯納工作室的學員,此當事老師之行為,恐已致迷惑混淆。
我在此謹向「台北邁斯納工作室」舉報以上事件,順請貴單位評估是否進行釐清事件的始末與關聯,以免在「不知情」的情況下遭受影響與損害。
台北 Meisner Studio - 台北邁斯納工作室
嘆,「勇氣」這件事啊,不但是自己要給自己,很難,原來,要拿勇氣去支持別人,更難。
《你為什麼決定說出來? 》
貼文後收到很多Me Too來信私訊,裏面有許多人告訴我,因為「同一位加害者」的霸凌,她們也出現身心症狀,必須接受諮商與治療。
是的,因他而生病的人除了我之外,不只一位。
這是促使我決定說出來的主因。
我很害怕自己接下來的人生,將與這位加害者的姓名永遠掛在一起,雖然Me Too來信者們同意我截圖公開她們的經歷,但是,我深深瞭解那種恐懼害怕以及無法預測的壓力。
所以,我不打算公開截圖。
我希望能以自身處理這霸凌事件的過程與方式,告訴所有的被害者:
「不需為加害者的惡行負責」
「不必因說出來而感到抱歉」
「說 與 不說,你都沒有錯」
我決定,獨自面對。
《這位霸凌者是》:
台北電影節 主席 易智言 先生
課程:台北電影節2022演員工作坊-進階
去年12/5 工作坊排練現場,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,北影執行單位有聘請攝影師在現場架設機器「全程錄影」,並且,被霸凌的演員同學,不只我一人。
也建請北影公開錄影檔並對外說明,以確保自清並維護權益。
若無說明,因受害者眾,本人不排除循司法途徑,提出「聯合訴訟」。
以此行動讓被害者們瞭解,我們同受法律保護。
是否提出聯合訴訟,端依北影的後續處理方式。
祈請北影不要以「將進入司法程序,不對外說明」的理由進行規避,因目前尚未進入司法程序,再者,本人無法確定本案是否有涉及「刑事或公訴」層面,望請慎重考量。
順請當事者誠懇面對,以止爭息訟。 決定權,在您。
此致 台北電影節
台北電影節 Taipei Film Festival
藍色工作室 Lan Se Production
其他記者提問之回答請見下段6/18更新文。
歷程紀錄:https://reurl.cc/514gzR
《備註》:
1、我原本今晚要出席北影的開幕活動(我想看九把刀的電影,6/12已回填出席表單,當時的我並不知道我6/15會發文)
但至目前為止仍未收到北影回覆入場的電子票券。 所以我不知道該不該去。
2、欸欸,黃舒湄,你被業界封殺定了!
「這點小事都承受不起,還『爆料淚訴』,誰敢再找你拍戲啊?」
「你掃到電影圈盛事等於跟全電影人作對,你完蛋了你!」
「如果進入司法程序,你連『本名』都要被公開,並且跟他掛在一起了,要死了你!」 ⋯⋯
(深吸一口氣)
沒關係了。 我未來的人生與工作,不管好與壞,反正,牙一咬,就過了。
「我不想成為像他那樣的大人」。
以上,謝謝大家,黃舒湄 2023/6/22
#登出地球的倒數十年 #權勢霸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6/18 更新文
先說明:《無辜者被誤解》一事
這證明了我的文章並沒有「刻意影射」的動機與意圖。
我原本就不敢說出加害者是誰,所以並沒有提供任何可辨識的外型、職業、背景、經歷⋯去引導加害者的身份指向某個範圍,只單純地描述事實與過程,也沒有使用煽動性的形容詞來誇大事件。
而且只要點開留言與分享內容,就會發現所有猜到的網友底下,答案都是「同一人」,並且留言者都在第一時間就解答。
「文章無影射、留言有解答」,
記者給我來訊也都明確指出加害者的正確姓名,所以,我並不認為有誤解的發生。
《但新聞標題的確去猜測無辜者了啊? 》
首先,
「被害者不需為加害者所造成的傷害負責」
當下的、後續的、衍生的⋯⋯都不需要。
再來,
這其實也只是新聞採訪或辦案偵訊的方法與技巧,是為了促使當事人說出真相的推力。
這是新聞工作者的職責,我能理解的。
《既然無影射,為什麼留言者猜得到? 》
只要點開留言與轉發分享者的發文內容,就會發現:
「他們都是跟加害者有共事或相處經驗的人」
其實我對這點也非常驚訝!
很多網友私訊我說:
「不意外、他也對我這樣、我們都退選了、沒看到一半,就從口氣態度語言,知道是他! ⋯⋯」
甚至有個網友說:
「我看到你寫『原子筆咔咔聲』就更確定了,那是我第一次發生恐慌症。」
我們連恐懼的觸發點都一模一樣!
這才是我決定說出來的主因。
《為什麼提到「麥斯納技巧」? 》
因為授課過程所發生的霸凌,是這位加害者口中所稱的「麥斯納」,我必須先說明麥斯納與方法演技的不同,才能解釋:
工作坊同學們在課堂上因為不瞭解這種技巧,所以「無法辨識」教學VS.霸凌。
我相信很多當時被霸凌的同學,甚至以為自己是在「接受挑戰」。
感謝鳳小岳先生的補充說明。
鳳小岳 Rhydian Vaughan
最後,
《要說就快說,賣什麼關子啊! 》
已經有網民開始留出這類評論了,
所以,我還是要說明一下,目的絕不是為了影射,而是不得不說出我的為難:
做出決定之後,才突驚覺業內有大活動即將舉辦,我很擔心會因此影響這個活動的焦點。
「什麼時間點說,才是最適宜的?」
我陷入天人交戰,不知道該如何決定,希望神給我指示。
然後,
媒體標題的「因1事」其實是因為最後這一點才對,換照片是因為,我喜歡這張照片。
以上,謝謝大家 6/18舒湄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6/15 原始貼文
最近MeToo風風火火,很多網民丟出:
承受不了就不要當演員、 這本來就是演員該做的事、那以後大家都不要拍戲了⋯⋯
很多人覺得,演員無限上綱。
我想跟大家說一個故事,這個故事裡頭沒有「性」,但我想說的是,霸凌有太多種形式,但是都含有相對的「權勢」,在權勢底下,被霸凌者都是恐懼而無助的。
以我一個恰查某的強悍,卻依然選擇噤聲的親身例子,來聊聊:
「能說出來,到底要多勇敢」
以及
「演員的工作必須要有界限」。
曾經報名一個徵選制的演員工作坊,當時看了授課師資的名單非常仰慕,獲選時非常開心,對這即將為期3個月的工作坊充滿期待。
授課老師選擇「麥斯納技巧」作為訓練內容,這種表演技巧與方法演技是相反路徑,對一般方法演技演員來說難度非常高,也非常難教,要洗掉過去的表演經驗,就已是非常困難的第一步,老師與學生都必須先經歷「講了聽不懂,說了做不到」的挫折。
這種師生挫敗感在第二堂課就被爆發出來,授課老師藉著練習的名義,現場與一位同學進行「互相攻擊」的對罵,當下情況接近失控並且沒有授課焦點。
果不其然,次堂課,我上場不到5分鐘,就被老師轟下台,說我太「演」,會拖累其他同學的時間,不讓我繼續做練習。
接下來說到的排練,有全程錄影。
進入劇本首次排練,我們這組被老師不停打斷,老師對我的表現很不滿意,用了各式激烈的情緒與嘲諷的語氣,他說,我是一個沒有range(彈性)的演員,讓他不知道如何指導我。
我努力配合老師給的意見不斷修正表演,他持續打斷、持續嘲諷,包括:
「你的表演讓我想吐(搭配嘔吐的表情)」、
「你是在演幾歲啊? 太噁心了!」
…… (還有很多惡劣語言我已經選擇性遺忘了),中間竟然還把我們叫下台,要求另外兩位從沒看過這個劇本的演員,「演給我們看」。 過程充滿嘻鬧與嘲笑。
幸虧我的對手演員向老師陪笑臉,而我也始終緊閉嘴巴沒有違逆,老師才讓我們再上台「試最後一次」。
這次他終於拋開謾罵,先給出明確的指令:
「你應該是一位溫暖自信充滿包容的女性。」
這下我心中完全明白老師「給了錯誤的指令」。
我們拿到的劇本是「愛在三部曲」的最後一部、最後一場,伊森霍克與茱莉蝶兒從首部曲相遇、二部曲相逢,到了三部曲是「相厭」,而這場戲,是茱莉蝶兒吵著要離婚,對伊森霍克大酸特酸,刻薄又討人厭,而我卻必須「溫暖自信充滿包容」?
我是職業演員,我就照著你的指令演,沒有問題。
終於完整走完唯一的一次,老師沒有打斷,因為我們的表演很好,聽對手演員說,有同學在台下看了掉淚。 這次,老師沒有辦法給筆記了,他只嗯嗯嗯了幾聲,說:「嗯… 欸… 算是裡面還可以的一次啦。」 接著讓同學們休息10分鐘。
我以為自己過了一關,休息時經過樓下,老師圍著一群演員同學抽菸聊天,老師遠遠看見我,就對著所有同學指著我的鼻子說:「主角來了。」
他竟然花了整節下課時間在跟「其他」同學「討論」「我的」表演。
他叼著菸把我叫過去,當著所有同學的面,劈頭說:「你是什麼背景的?」
我低著頭簡單說明一下。
老師:「所以嘛! 我說得沒錯,你根本沒什麼表演經驗。」
我持續低著頭沒有回話。
老師:「你的表演有一種『窠臼』。」
我將腰屈得更彎,請教:「老師,請問是什麼窠臼?」
他無法解釋:「反正,就是一種窠臼!」
他搖搖手叫我離開,繼續抽他的菸。
我天真以為自己是在打一場艱苦的硬仗,這下我才完全明白:「我在打的,是一場必輸無疑的敗仗。」
不管我的表現好不好,他都會把我說成「爛演員」,就如同他現在圍著「別人」討論我一樣。
當天晚上我回到家,對於自己報名了這個工作坊感到後悔,擔心這會傷害到我接下來的工作,我開始非常焦慮。 我打開手機、電腦、筆電,把所有為工作坊所做的survey全部刪除,把我的瀏覽紀錄裡有他名字的資料,逐筆清光,我不敢看到他的名字,那3個字只要出現在我的視線,我就害怕到顫抖不已。 當下,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:
「放棄好不好? 不要再去那個工作坊了!」
我完全理解那些因為霸凌而不敢上學的小孩了,我只想躲在家裡,不要見任何人。
我失眠、心跳超過100,短短幾天就瘦了5公斤,於是去看了身心科,醫師建議我不要再繼續這個工作坊,甚至還替我開了證明。 但是,他也說了:
「你更可以安安靜靜地退出,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,因為公開病歷,你會遭受到更大更未知的壓力,對很多事不關己的人來說,是無法同理的。」
但是,我的對手怎麼辦?
我仍舊選擇跟對手繼續工作,面對課程表定的最後一次排練。
試煉還是繼續來。
就在我跟對手排練的當時,傳來訊息:
「老師確診了。」 執行單位說:「老師出關後,會跟每組一對一排練,請大家給出另外的時間。」
當下我跟對手緊急核對時間表,沒想到,我跟對手可以的時間老師不行,而老師可以的時間我跟對手無法集合起來,距離呈現演出只剩下不到10天。
在執行單位追殺逼時間的高壓當下,我的對手也焦慮地說:「我不懂,事情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?」
執行單位中間對我的誤解與責怪就略過了,為了不要再繼續造成誤會,當他們提出要我空出原本沒有安排的進劇場時段,我盡力配合,也趕到了。
是的,還有接下來。
演出前一天進劇場spacing結束後回到家,我接到對手的來電。
他說,老師「很溫柔地」跟他說:「明天,我可能不會讓你們這組上台。」
他的原因是:「因為明天來現場看呈現的,都是導演跟選角,『如果』你們兩個表現不好,對你(指對手)反而會是傷害,我是在『保護你』。」
我聽完陷入崩潰邊緣。
我跟對手都是入圍過的演員,但是,沒有一個現場觀眾看過我們這次的排練,「不能上台」只會造成更大的揣測,我們「表現不好」到什麼程度? 只能任人遐想與臆測。
「表現不好所以不能上台」,這一切都是老師說了算,這對我們將會是多麼大的傷害?
我幾乎要哭了說:「不能上台,我們就沒有證人,這更傷! 明天我們去求他! 拜託你施展你的可愛,讓他喜歡你! 那如果他真的要我去跪,我願意在所有人面前向他下跪,只要他肯讓我們上台!」
對,當時的我什麼都可以不要了,不但想拿我對手的可愛去換! 我自己更願意交出最後的自尊向他跪下!
那個晚上,是我最難熬的夜晚,我想了各種不能上台的因應方案,我甚至想,「到時自己衝上台直接演」,如果我的對手不敢上台,我就自己演,我做「獨白」! 我連獨白的台詞都準備好了。
「我們必須要有證人」,這是我心中唯一能想到的事。
第2天,我吃了雙倍的抗焦慮藥到現場備戰。 可能就是因為當天的技彩排是公開的,現場不但有同學,還有劇場的工作人員;
「因為有證人」,所以最後我們還是上台了。 但是當晚觀眾絕對沒有人想像得到,我當時是在什麼樣的心理狀態,吃了多少藥,才有辦法完成這個演出。
這件事對我來說,除了老師在我身上所施加的霸凌之外,對我影響更大的創傷,還來自「個人的尊嚴剝奪」以及「團體的歧視切割」。
那3個月裡面,我嘴巴緊閉不作任何抗辯,不讓權勢有任何藉口指稱是我的責任,同時還必須在團體裏面假扮弱勢,以求維持對手的信任。 「村八分」是最可怕的刑罰。
許多網民把這個議題鎖在:「演員沒經驗、演員玻璃心」上面,開始檢討被害者。
身為有經驗的強悍演員以及表演老師,我必須要向大家說說,演員的脆弱從何而來:
演員的《正式拍攝》V.S.《前置排練》,兩者是完全不同的狀態,《正式拍攝》時會面臨到時間緊縮、環境干擾、精神壓力... 等因素,所以演員在拍攝現場,會開啟「備戰模式」,讓自己的Body-Mind被影響的程度降到最低。
《前置排練》,則不然,為了創造表演的各種可能性,演員必須反過來卸下所有的防備,像是掀開頭骨的腦漿、剖開肚皮的腑臟,以最赤裸、最開放的態度,全然接收,擁抱被重塑、被再造。
所以「排練當下」,是演員最脆弱的狀態。
如果引導者拿著這份權力任意地予取予求,踐踏演員的信任事小,最嚴重的是把演員的Body-Mind侵蝕了、啃噬了、摧毀了,這部分是沒有機會重來的,因為那跟「生命」綁在一起,是職業演員「唯一」的本錢。
所以,當一個演員願意以最赤裸脆弱的狀態跟引導者排練,那絕對是自願的、是信任的,引導者怎麼可以不珍惜這份信任? 不保護這份脆弱?
更何況這個人是老師、是導演、是掌有權力的人!
演員為戲受傷害,是醜聞,不是發新聞,
演員為戲來真的,不是敬業,是不專業。
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職業,應該要為工作受傷、犧牲、脅迫、甚至死亡。
會計師不需要為數字犧牲,律師不可以被法律脅迫,警察不應該因工作殉職,那麼,請不要要求演員要為表演付出生命、犧牲健康、放棄尊嚴,甚至為了戲被甩3百個巴掌。
那是綁架勒索、那是集體霸凌。
希望網民不要再把「這是演員本該承受的」這樣的指控套在被害者身上,沒有人應該承受這些事。
你為什麼不拒絕? 你為什麼不說出來? 你為什麼不檢討自己? 你為什麼小題大作? 你為什麼玻璃心? 你為什麼不敢大方具名?
你、為、什、麼、不、反、抗?
讓我這個恰查某告訴你,
因為,「害怕」。
連我這麼強悍,都怕。
所有的霸凌,都跟權勢掛在一起,因為不對等的關係,被害者恐懼權勢,害怕不服從所帶來的毀滅效應,當權勢者提出要求時,被害者往往選擇的是「此刻就毀滅自己」,根本無法思考自己交出去的是「財產」、是「工作」、是「尊嚴」、甚或是「性」。
就跟黃云歆寫得一模一樣:
擔心自己蹭新聞、說了沒人理、被笑小題大作、反而被輿論檢討、被算帳、因此丟工作…… 最後玉石俱焚。
我一直以為我遇到的權勢霸凌事件只是「茶壺裡的風暴」,走過就會好,直到今年拍戲,我才發現我依然沒有好,聽到原子筆的咔咔聲,我竟然會感到害怕(那位老師在課堂上會不斷地壓原子筆),他依然在影響著我的人生,我的工作。
而這個執行單位接下來所辦的各種活動、各種新聞,我都不敢看、不敢參與,覺得此生與這個單位所舉辦的獎項從此無緣,再遇到當時同班的同學時,我更是覺得無地自處、沒有自信。
原諒我,寫到這裡,我依然不敢說出那位霸凌者的姓名,因為,我只要想到,「自己的名字將會跟他連在一起」,我都會感到恐懼害怕。
我是恰查某,連我都這樣了,所以「勇敢說出來」這件事真的沒有那麼容易,希望網民能高抬貴手,停止二次傷害,也祝福被害者們,暗夜不要再聽到「咔咔聲」。
#MeToo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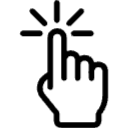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






